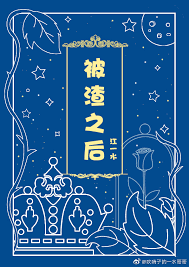手机浏览器扫描二维码访问
第1章 憨死的社畜(第2页)
王大柱艰难地转动眼珠,目光扫过这八张或明艳、或娇俏、或温婉、或英气的脸。她们穿着同样喜庆的正红嫁衣,站在这间充斥着“囍”字窗花和红烛的、布置得俗气而拥挤的新房里,像八朵被强行移栽到同一盆里的、习性迥异的花。大太太周氏——后来知道她闺名周婉娘,陪嫁里据说有半个县城的铺子,管家的手腕铁一样硬。二太太柳莺儿,原是个小戏班的台柱子,嗓子甜,身段软,心眼儿活络得像泥鳅。三太太林红缨,镖局武师的女儿,据说一拳能撂倒一头半大的牛犊子,性子也跟她的拳头一样又硬又直。还有四太太、五太太……身份各异,但无一例外,都是王老抠用真金白银,在王大柱“昏迷”期间,像采买货物一样迅速置办进来的。
荒谬!巨大的荒谬感像潮水般淹没了王大柱。别人穿越要么是王侯将相,要么是天才修士,再不济也是寒门书生,王大柱呢?员外家的傻儿子,附带八个刚进门的、彼此间火花四溅的、目的不明的老婆!这开局,简直是地狱级的生存挑战。
日子就在这种鸡飞狗跳、暗流涌动的诡异氛围中滑了过去。身体渐渐好转,王大柱也被迫开始扮演“王大柱”这个角色。大太太周婉娘果然不负众望,账本每天雷打不动地送到王大柱面前,条目清晰,数字密密麻麻。她站在一旁,也不多言,只等王大柱翻看,眼神平静无波,却带着无形的压力。王大柱硬着头皮,凭着前世那点可怜的财务知识和原主记忆里关于田亩、佃户、收成的模糊概念,半蒙半猜地看,偶尔壮着胆子指出某个租子数目似乎偏高,或者某笔人情开销显得过于豪奢。周婉娘眼中第一次掠过一丝极淡的讶异,随即点头:“相公说得是,妾身再核。”语气依旧平淡,但那点讶异,让王大柱心头微松。看来这傻儿子的“傻”字标签,并非牢不可破。
二太太柳莺儿则像只花蝴蝶,整天在王大柱眼前晃悠。今天捧来新染的布料,非要王大柱摸摸评点;明天端来一碟她亲手做的、甜得齁死人的点心;后天又对着铜镜哀叹自己新得的一支簪子样式不够时兴……她的热情像滚烫的糖浆,黏糊糊地裹上来,目的明确——要钱,要关注,要拔高她在后院的地位。王大柱疲于应付,只能含糊其辞,或者干脆装傻充愣,眼神放空,嘴里嗯嗯啊啊。
至于三太太林红缨……她绝对是行动派。自从王大柱勉强能下床走动,她“强身健体、守护家业”的魔鬼训练就开始了。天刚蒙蒙亮,她准会出现在王大柱卧房外,抱臂而立,像一尊门神。“相公,时辰到了!”声音不大,却带着不容置疑的穿透力。然后就是枯燥到令人发指的扎马步。那酸爽,简直让人怀疑人生。大腿肌肉疯狂颤抖,汗水小溪般往下淌,眼前阵阵发黑。她就在旁边盯着,姿势稍有变形,一根细长的柳条就会毫不客气地抽在王大柱腿上,火辣辣地疼。
“腰沉!肩松!目视前方!脚跟钉在地上!你抖什么抖?没吃饭吗?就这身板,土匪来了你跑都跑不动!”林红缨的声音又冷又硬。
王大柱咬着牙,心里疯狂吐槽:前世九九六好歹还有张椅子坐!现在倒好,直接站桩!土匪?这太平盛世的哪来土匪?她就是想找茬!但看着她那绷紧的小臂线条和锐利的眼神,反驳的话到了嘴边又咽了回去。这女人,真敢下手。
后院成了王大柱唯一的避风港。这里远离前厅的喧闹和姨太太们争奇斗艳的硝烟。几畦菜地绿油油的,角落搭着个简易的鸡棚,几只芦花鸡悠闲地踱着步,“咕咕”地叫着。空气里飘着泥土和青草的气息,还有一丝若有若无的……鸡粪味儿。这味道对前世闻惯了汽车尾气和写字楼消毒水的王大柱来说,竟带着一种奇异的安抚力量。
王大柱蹲在鸡棚旁,手里摆弄着几根长短不一的竹竿和麻绳。这不是闲得慌,而是前天看到染坊送来的布匹时,一个念头突然蹦了出来。这个时代的织布机,效率低下得令人发指。王大柱曾偷偷溜去织工那里看过,老式的腰机,全靠人力往复投梭、打纬,织一匹布耗时耗力。如果能稍微改良一下……前世虽然是个码农,但基本的杠杆、滑轮原理还是懂的。王大柱试着用竹竿模拟悬臂,用麻绳充当简易的提综装置,试图构思一个更省力、能提高一点效率的结构。
“相……相公?”一个怯生生的声音在旁边响起。
王大柱抬头,是八太太,年纪最小,才十六岁,叫翠儿。她手里端着个粗陶碗,里面是冒着热气的米粥,眼神像受惊的小鹿,飞快地瞟了一眼王大柱手里那些乱七八糟的竹竿绳索,又赶紧低下头。“大姐……让、让妾身给您送早饭。”她声音细若蚊呐,放下碗就想跑。
“等等,”王大柱放下竹竿,尽量让语气温和些,“翠儿,别急。你……识字吗?”
翠儿猛地抬头,大眼睛里满是惊讶和惶恐,随即用力摇头,小脸涨得通红:“不、不识的!妾身……妾身只会烧火做饭,喂喂鸡鸭……”她像是犯了天大的错,绞着衣角,头垂得更低了。
王大柱心里叹了口气。这个时代,女子无才便是德,尤其底层。看她紧张的样子,王大柱放缓语气:“没事,我就问问。这米粥看着不错,谢谢你了。”她如蒙大赦,飞快地行了个礼,转身小跑着离开了。
王大柱端起那碗温热的米粥,粗糙的陶碗硌着手心。目光扫过那些简陋的模型,再想想前厅那本厚厚的账册,二太太永远不满足的索求,三太太冷酷的柳条……一股强烈的无力感涌了上来。这员外家的傻儿子,真不是那么好当的。王大柱想做的,不过是安安静静地待着,琢磨点能改善生活的小东西,远离那些纷争算计,怎么就这么难?
就在这时,一阵极其不和谐的喧哗如同平地惊雷,从前院方向猛地炸开!那声音尖锐、混乱,充满了原始的暴戾,绝非王家日常的动静。男人的粗野吼叫、杯盘器皿被狠狠砸碎的刺耳脆响、女人惊恐到变调的尖叫……各种声音混杂在一起,像一把冰冷的锥子,狠狠扎破了后院这片勉强维持的宁静。
“抢粮!抢钱!把值钱的都交出来!”
“王老抠呢?叫他滚出来!”
被渣之后
尹白曾经以为,萧念是真的爱她。所以拱手送上最好的资源,将她捧上了神坛。功成名就之后,萧念为了真爱,一脚把她踹了。 尹白成了娱乐圈里最为让人耻笑的金主。 萧念获得影后桂冠当晚,当着尹白的面官宣了此生挚爱,气得尹白转头到了停车场,拿着拐杖砸得自己的车邦邦响。 好巧不巧,这个尴尬的场面被萧念的死对头左静幽看到了。 尹白当场收了拐杖,轻咳一声整理袖口,若无其事地打了声招呼:“好久不见,左小姐。今天的天色,真不错啊。” 左静幽一脸淡然,十分镇定地说:“尹总请放心,我什么都没看到。” 左静幽说完这话,和尹白擦身而过,气得尹白当天晚上差点没把拐杖打断。 几天后,尹白在医院的长廊上遇到左静幽和人起了争执,对面的男人红着眼说出了一句名台词:“你失去的只是一个不爱你的丈夫,他失去的一份真爱啊!” 尹白脚步一顿,恰好对上了左静幽深沉的目光,于是善解人意地比了个口型:我什么都没听到…… 尹白:我以为我是那个驯养玫瑰的小王子,到头来,我发现我不是,我只是拥有四根刺却觉得自己能为所欲为的小玫瑰。 左静幽:我以为爱情里,只要我做的足够好就可以了。可是爱情并不是那么简单的事,只有一个人做好,是不够的。 所以这一次,我会学着好好爱你。 注:攻跛足,身上有伤疤,对自己有情感洁癖。 受离婚,一个人带着孩子过。 非双洁。...
妖年
北燕三十二年秋,先有天上陨石坠落皇城外山上,后有民间怪事不断,但最引人风头的,还是文渊阁首席大学士家中的混世公子,在满城与人津津乐道的作妖之事,因此这一年,也被后世的人,称之为妖年……...
熊猫王国
汶川大地震失踪的小小,和白雪在野外产下的儿子白朗,在卧龙深山,建医院办学校,和人类贸易,发展生态旅游……......
阿哥的员工不好当
阿蘅醒来已经是另外一个世界,魂穿到百年前的清朝她以为提前知晓未来的开挂人生开启,没想到康熙的几个儿子不是幼稚鬼就是腹黑男好不容易来到古代不用上班却又要给几个阿哥打工一下子多了九个老板......
肆意撩拨
【实战派风流忠犬总裁攻vs微钓系高冷理智医生受】 帝都名流圈里谁不知道林邵泽是个玩的开的,但就算玩的再开的人,也会遇到自己的报应。报应到了的时候,想拦也拦不住。 见狐狸崽的第一见面,林总就知道这人是在自己的审美上蹦迪。 只是可惜撞号了,但这不重要。 宽肩窄腰,不苟言笑的拒绝,愣是勾起了林总浓厚的兴趣。 然后.....然后林总就被拉黑了。 层层接近下发现,这冰山狐狸崽竟然还是个抢手的! 前男友、青梅竹马一个接一个的蹦出来,就连自己的前任都喜欢上了这狐狸崽。 昔日情人变情敌的戏码,林总是万万没想到还能发展到自己的身上。 ...... 但报应终究是报应,爱而不得,终归是对他以往风流的惩罚。 自不量力、盲目自信终究还是把这份感情推到了绝路。 那整整三年的日日夜夜,情话和思念全都泛滥成灾,可狐狸崽却没有回应哪怕一句。 三年后再见面,我一定不会再放手。 * 夏冰活了这么多年,追求者众多,但很显然,称得上不要脸的唯林邵泽一个。 原以为他这样的花花公子没什么值得托付的,可这人总是在自己最需要的时候出现。 每一次交往,都会发现不一样的他。 或许在这风流不羁的外表下,真的有一颗忠犬的心。 三年的惩罚,对你来说够了。 【提示:攻受均不洁,受为爱做0、1v1、不清水】...
京色欲坠
连厘父亲是顶级财阀靳家的司机。父亲殉职那日,瓢泼大雨,靳言庭朝她走来,磁沉嗓音落下:“跟我走。”他把她带在身边,一护便是九年。听闻靳言庭为了白月光差点和家里闹翻,连厘深知他心里没有她,选择体面退场。熟料月色缱绻,厮混整夜。翌日晌午,睁眼醒来,身畔是他亲弟弟靳识越。连厘诚挚建议:“昨晚你也很尽兴,不如好聚好散?”“没......